熟悉英文、日文、俄文和法文,年过八旬居然又开始学习德文,参与共和国最早的民法起草工作,曾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法律顾问、特种常规武器裁军大会代表团法律顾问和原对外经贸部特聘WTO法律顾问,是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成员指示性名单上的中国专家,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副主任……这就是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的董世忠先生。
2017年7月初的一天,我们复旦法学院校友会几位同仁前往先生家探访。先生精神矍铄,思维敏捷,全然不像一位耄耋老人。

△ 董世忠先生在校友来访时热情交谈
先生祖籍宁波,1934年生于扬州,他的读书生涯也始于扬州。那时候先生读的是私塾,日本人占领扬州之后,强迫小孩子学日文。也就是这个时期,先生开始了他的外语学习生涯。抗战胜利之后,先生回到宁波,在教会学校上小学和中学。这个期间,他开始跟着一位传教士家属学习英文,直到1949年解放。
刚刚解放时,宁波仍然算是前线。当时国民党军队盘踞在舟山群岛,他们不甘心失败,不断派出飞机轰炸。当时丢的炸弹不是一般炸弹,而是燃烧弹,丧心病狂的轰炸让宁波大半个城市常常陷入火海之中,学校停课。无奈之下,先生只好来到上海,在一家化工原料企业做学徒。
回忆起这段经历,先生说还要感谢在宁波时读的英文。当时,初中毕业就算是知识分子了,化工原料中,英文和拉丁文字母特别多,要用英文打字,领导试着叫他做,没想到他一上手就做得非常出色。
“新中国刚刚成立,百废待兴,大家劲头都很足,整个社会一派欣欣向荣。”先生说,“化工企业是早上9点上班,下午5点钟下班,我一早6点半就去立信会计学校读书,上到8点多回来上班。当时学的是会计、审计和统计等科目。5点钟下班后又去上补习班,补习数学、物理、生物,整整用了4年时间,我读完了会计,也补习完了高中课程。”就这样,先生于1954年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。当时,国家非常需要法律人才,院系调整时,复旦大学和安徽大学等学校的法律系都合并到华政,先生读大学那年正是经过院系调整以后华政第一次招收本科生。

△先生在华东政法学院就读时的记分册首页

△先生年轻时热爱田径运动,图为他当年的运动员、裁判员证书,是先生非常引以为豪的物品
先生说,和法律结缘终身,实属偶然,可是一旦情定,终身无悔。先生还说,一个崭新的国家,需要崭新的法律体系。自己能成为其中一份子,十分荣幸。法律是面向社会实践的学科,先生回忆说他们读大学时考试没有笔试,全部是口试。考试的时候三个老师坐在那里,面前摆了很多题目,考生自己去抽,抽到哪道题就答哪道题,题目有概念性的东西,涉及法律实务的也有。
先生毕业后,因为成绩优异留校做助教。他助教的课程是海商法,上课的是从美国回来的专家魏文翰先生。魏先生在抗日战争的战前和战后,被上海商界称为是能保护华商海运界的大律师,被学界称为法学教授、海商法的权威;而在抗战期间,后方的政界工商界也都知道他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协理、代总经理。就这样一个学术实务兼备的大师,被先生幸运地遇到了。
遇到魏先生之后,先生真的跟海绵遇到了水一样,他既是助教,也是学生,这期间,他逐渐对海商法和海洋法有了系统的学习,也决定了他的研究方向。
若说魏文翰先生是在先生法律生涯中产生影响的第一人,那么第二人和第三人则分别是张企泰先生和杨兆龙先生。张企泰,法国留学归来,民法和罗马法专家,拉丁文非常好。杨兆龙,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,后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,通晓英、法、德、意等八国语言语,对大陆、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,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。
“当时有个说法,要把老先生的东西都学过来。我要去做这个学过来的人,这就是我在去北京做民法起草工作前这段时间做的事情。”先生回忆说,“三位老师都是享誉国内外的法学家,在1958到1962年这4年的时间里,我受益匪浅。”
1959年初,华政撤销并到上海社会科学院。先生当时在学术秘书处编写国外的法学动态,他英文好,编写的国外法学动态得到当时的政法研究所所长、后来的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元岑瑞先生的肯定,他派先生去华师大进修英语。
“去华师大进修期间,上午学英语,下午回来工作,工作也是把外国的资料翻译成中文,编辑成简报,给其他研究人员看。在给那几位老先生做助教时,我有很好的机会学习法律英语。”
成就一个人的,是他的经历。先生的英文基础、先生在立信会计的学习经历、以及先生华政期间的法律学习,最重要的是,先生对知识的孜孜以求,共同成就了后来世人心目中的那个董世忠先生。
初担大任 初露峥嵘
先生是1963年到1964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参与民法的起草工作的。当时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成立民法起草组,起草组的成员由各个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的教师组成,一共10多个人,再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,共同起草民法,先生成为其中之一。
起草中,需要找国外的资料,法律英语呱呱叫的先生又成为了顶梁柱。先生记得,当时主要参考的是前苏联、德国、法国和瑞士的民法典。在这个期间,查资料非常便利。可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到各个地方调取材料,人家都没有二话的,全力支持。
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多的工作中,先生系统地学习了外国的民法。先生回忆说,那个时候,大家都不讲合同,都讲关系,比如买卖合同叫买卖关系,租赁合同叫租赁关系等等,这个都是时代的烙印。
1972年华政并到了复旦,老师分到各系做指导员,先生当时分到国际政治系。“国政系人称第二外语系,当时很多人说董世忠只懂英语,就让他去国政系。这话听听也就算了,我也不放心上,到底是不是只懂英语,自己知道就行了。”先生风轻云淡地说。
那时国政系办了一个工农外事干部培训班,先生被派去教英语。学校特批给外语教师一个特权,可以听外国的电台。得益于这个特权,先生的英文听力和口语突飞猛进。再加上后来带参加培训的干部去涉外旅行社实习,有了和外国人直接接触的机会,使先生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△先生在国政系工作时取得的荣誉
每一次机会都是他的饕餮盛宴
改革开放,春风吹来。人们如饥似渴地睁开眼睛看世界。上海得风气之先,国家要派人学习西方的世界经济,在复旦选了两个人,先生是其中之一。
先生被派去的是日内瓦国际高等研究院,这个研究院专门培养外交人才、国际经济人才和国际法人才。先生当时的身份是访问学者,访问学者听听课,完成课程之后回国就算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了。但先生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,白天在研究院上课,晚上补习法语,终于通过研究生考试成为研究海洋法的正式学生,他的毕业论文《中国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的立场》也是用法语通过答辩的。
读书期间,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。王铁崖教授是与会代表,先生因为既懂法律英文又好被王教授推荐给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。

△ 董世忠先生参加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时的代表证
“联合国有四种语言,其中英语最重要,联合国的文件范本也是英文,再把它翻译成其他文字。正式开会的时候,会讲法语,讲西班牙语,讲中文,配同声翻译,但在非正式谈判时都用英文,比如谈判碰到问题了到咖啡馆喝杯咖啡,说的都是英文。”先生说。
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。说起这个公约对我国的意义,先生说:“成果当然是有的,最主要的是对南海问题没有讨论,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,当时南越提出这个问题,我们把它否决掉了。现在谈到南海问题,南海问题在联合国公约中找不到规定,但联合国公约前言讲得很清楚: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,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。所以,你别个国家仲裁怎么样,超越不了也凌驾不了这个规定。”
如果那个时候把南海问题真的拿出来讨论会怎么样?面对这个问题,先生徐徐作答。他说,当时讨论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们有利。你想想看,三亚到南海最南端岛屿的距离相当于三亚到哈尔滨的距离,当时我们海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,而且当时考虑到战略问题,更多地关住马六甲海峡,是后来才发现南海下面有石油、燃气、可燃冰。当时小平同志提出来搁置争议、共同开发,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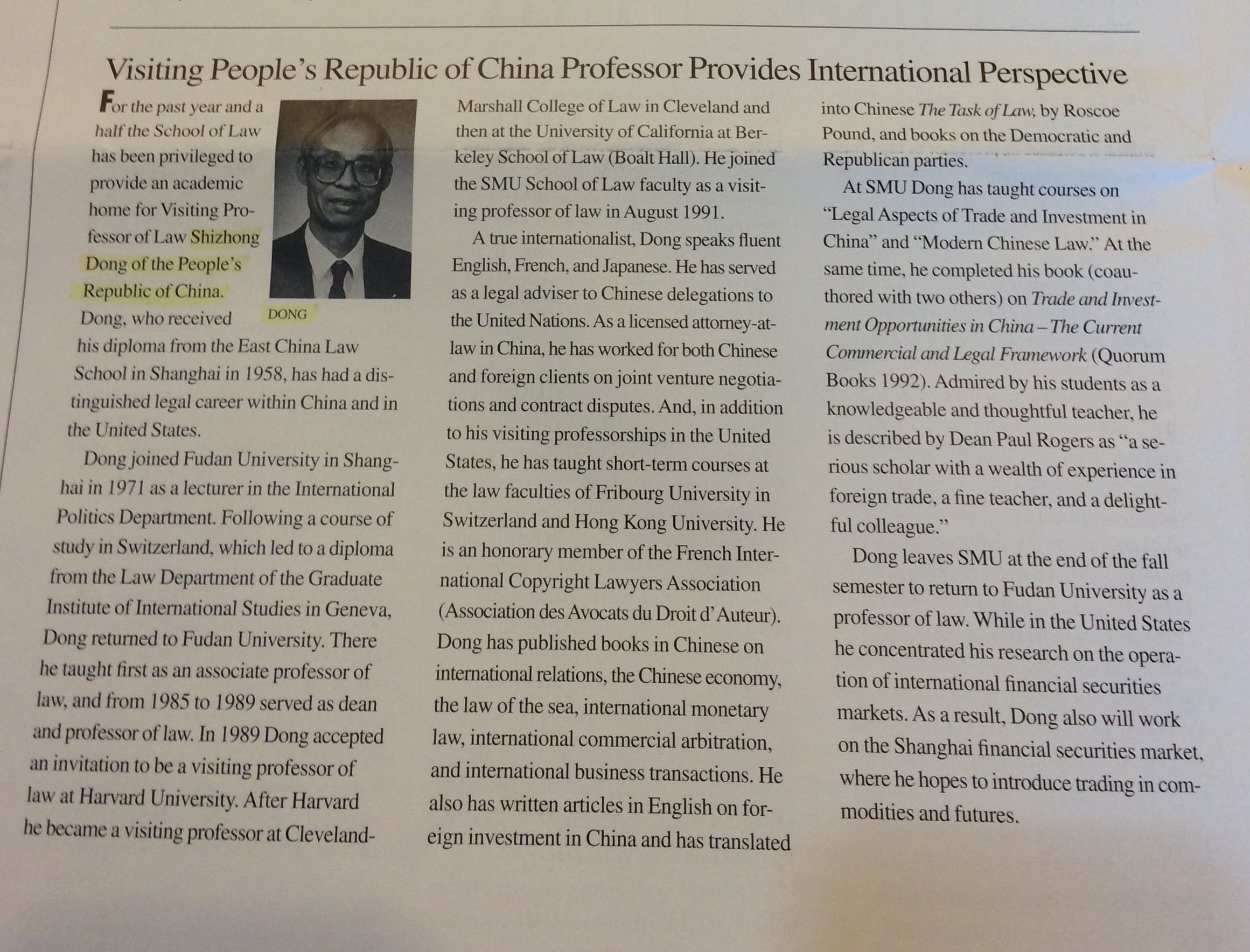
△ 1992-1993年度School of Law of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的 News Letter 对先生的报道
说起海洋问题,先生滔滔不绝。1958年中国宣布领海12海里,12海里是讲了,但是从哪儿算起啊?基线没有公布,美国人采取的办法是每天开军舰来停一停,试一试你的底线在哪里。当时我军对美国军舰的警告很多的。总的来说,我们以前对海洋的重视不够,而人家早就在那里盯着了。他还说,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对我们是不利的,最有利的是那些面向海洋的国家,比如澳大利亚,比如我们和日本之间不到400海里,必然会有重叠的部分。重叠部分有两个处理原则:一是日本提出的中间线原则;二是我们提出的公平原则和历史原因。我们还讲到海洋的自然延伸(natural prolongation)。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,像钓鱼岛,冲绳海沟就都属于这个问题。
春江水暖 亲历上海大众最艰难的谈判
1981年,先生作为法律顾问参加了大众汽车合资项目谈判。上海大众是我国最早的外资企业,谈判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合同适用哪国法律的问题。德国人说,适用德国法你们不会同意的,提出来要用瑞士法。先生认为与合资企业相关的合同不能用外国法。德国人说,那你说用什么法?先生想了想说,先空着。德国人说,空着怎么行?先生说,碰到什么问题用最密切联系原则。德国人就和谈判组的负责人说,你们这位律师到瑞士去学习,竟然不相信瑞士法律是公正的,让人难以置信。先生回应说,不是不相信瑞士法是公正的,是因为这个合资企业和瑞士法律毫无联系。这是这一轮谈崩的第一个原因,第二个原因是市场保护的问题,德方要求上海大众不能出口到德国大众已经有市场的国家去,先生经过查阅发现,如果是这样,那么上海大众的产品除了柬埔寨和朝鲜以外,其他国家都不能去;第三个原因是采购要通过德国大众,先生说这不行,这不就垄断起来了吗?上海大众还有什么出路?
有了先生的这些“筹码”,德国人打道回府了,很多人都说是董世忠把事情搅黄了。先生挺有压力,但他觉得原则性的问题不能让步。一年之后,德国大众又回来了,继续谈判,先生提出的很多条件都写进了合同里。
和WTO的一世情缘
在日内瓦读书期间,先生开始接触到WTO,当时叫GATT(关贸总协定)。他读书的日内瓦国际高等研究院和GATT是在一起的,学校的图书馆就是GATT的地下室,先生的很多老师是GATT的工作人员,连GATT总干事也是研究院的兼职教授,时常来给他们上课。
到1981年和德国大众谈判期间,先生碰到外经贸部的官员,“痛陈”加入GATT的各种好处。1984年底1985年初,汪尧田教授提出来要恢复GATT的席位。汪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老专家,外贸学院的教授。他牵头成立了关贸总协定民间组织——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。1985年,外经贸部说要参加关贸总协定,那个时候开始谈判,先生和汪先生他们提出三个原则:一是我们是复关,不是入关;二没有进口承诺(import commitment)(指每年要承诺进口WTO成员国多少东西,而且这些数字要随着GDP的增加相应增加),而用关税减让原则;三是以发展中国家资格加入。如果是发展中国家资格加入,可以避免很多伤害。比如WTO第19条,如果国外的产品大量进口,对国内行业造成重大损害(material injury),你可以停止进口。
“比如你进口原材料,你适用的不是最惠国待遇,而是正常关税,这是好处;坏处就是互惠,给人家好处,人家也进来了,但是我们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,对于哪些部门能开放,我们用正面清单,而不是负面清单。还有个发展中国家的好处,非互惠待遇,你要降低关税,我不用降低关税。”
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时,正是我国加入WTO谈判最胶着的时候。当时很多人很激愤,认为美国欺负中国,我们还加入WTO这个美国人控制的富国俱乐部干啥。“我当时认为已经谈了十几年了,不能放弃,政治是政治,经济是经济,放弃了就前功尽弃。一个国家如果要工业化全球化,离开俱乐部是没有出路的。”先生当时和数位专家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,谈了他们作为WTO学者的想法和意见。
“其实,我们国家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好处,先生津津乐道,“我们穷的时候要出口创汇,以前中国人到外国去旅游,没有外汇,人民币在外国不能流通。我们那个时候出国,亲朋好友到我家来送我,不一样啊,现在拿了背包说走就走,为什么,我们现在富了。”
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成员之前,先生曾经被国家推荐为WTO上诉机构法官,和他同时被推荐的是前外贸部条法司的官员张月姣。每个国家代表团都会约你谈,欧盟、日本、美国,甚至我国的台湾地区代表都会约谈。法官看重的是你的独立性,看你当选后立场是否能和本国政府保持距离。后来他们两位都被列为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仅有的19位成员之列。
访谈结束时,我们请先生送给复旦法学院的新老同学们几句话,先生认真地想了想,然后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们复旦的法科教育要办出复旦的特色,祝愿大家成为懂外语、懂法律、懂经济的人才。”

△ 先生回到我院参加“法律人之夜”活动
让我们向耄耋之年还在学习德语的先生看齐,也向先生的寄语看齐。
采访人:张蓉、李瀚奇、吕萍
撰稿人:张蓉、李瀚奇
校 订:汪奕、陈鹏强